作为历史研究者,以及游戏档案馆的主理人,我看到这两天版署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及它引发的如沸物议,一直有种恍惚感。
恍惚是因为,作为一个历史意识与历史资源极其丰富的民族,我们本应非常擅长以史为鉴的。但实际上,大家也可以观察到,中国游戏几乎没有产业的历史意识,游戏的历史与档案流失都极为惨重;在社会层面游戏的种种问题更仿佛毫无历史基础,每次的讨论与认识都近乎从零开始。--而这个产业,从1994年的《神鹰突击队》和《Game集中营(创刊号)》算起,到这个冬至时,已近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该迎来成熟的这一年,在冬至迎来了《意见》的发布。公正地说,这是一份2019年文化部颁布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被废止之后,早该发布的文件。游戏产业的管理权与主管部门在过去十年间曾一再动荡,而这造就了游戏政策长期以来的不稳定性。《意见》的颁布,至少填补了行业管理规范的空白,让游戏产业能在有更明确管理规范的情况下存续发展。可以说,这份意见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它的发布。
《意见》中的规定,涵盖网络游戏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引导性、鼓励性的政策基本在于观念的表达(第四十九到五十二条),限制性的政策则非常清晰。其中关于消费的限制、对买卖版号的限制、对赌博游戏的限制,可以看到政策立意上都是为了刹清不正之风,是希望为产业的长期发展考虑的。第四十九条规定说“出版主管部门保障、促进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与繁荣。”细看《意见》的条例,也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良好的愿望。
但是,这份《意见》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可改善的问题。游戏的人档案馆可能会在之后以公益的身份递交意见,不在此深入细节,仅在此略为讨论。
我们认为,《意见》在两个方面可以优化:
第一是关于游戏及其相关概念缺乏深入研究,造成的打击范围泛化。目前行业的恐慌与社会舆论的不安,更多是由于“网络游戏”、“游戏沉迷”、“强制战斗”等术语与核心概念的界定范围不清,因而本来针对其中某些不法行为的打击,就有很大可能导向对正常经营活动,乃至个人正常娱乐活动的干扰与侵凌。这固然是和游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现状相关,也和教育部门并未实质性推进关于游戏的理论研究或素养教育相关,并非版署一个规定能够解决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至少能部分地推进概念的澄清,避免模糊概念造成的毫无必要的损失。
第二,是在政策落实的层面,能否向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这一问题其实也和第一条相关,核心概念的模糊,有时候可以建设性地保留一些“留白”空间容纳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但也容易导向现实行动无法推行。例如,关于版号一年为期的规定,看起来政策动机是为钳制买卖版号的不良产业风气,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会极大增加审批部门的行政负担,也会带来更大的行业杂音。游戏版号的审批,需要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也需要更明确的标准。列出负面清单,限制不良行动是监管部门尽责的表现,但是与此同时,积极的、引导性的政策也是执行必备的。例如,既然版号的存续期缩短了,是否可以多放版号?合规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是否也可以列入政策?既然提倡精品原创游戏的发展,那是否可以配套相应的版号政策?
第四十九条规定清楚写明,“出版主管部门保障、促进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我认为这是一条极其可喜的规定,因为它真正把产业的发展与繁荣纳入了政策。那么,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我也想基于我馆作为(自命)产业德鲁伊,在游戏产业及社会领域建设正向价值时,逐渐意识到的一个体系性的问题,来最后说几句。
中国游戏产业,虽然即将而立之年,却并称不上成熟。我们喜欢使用生态学的概念来理解这个产业,简单地说,游戏产业的大生态与小生境都不太完善。无论是环境本身的稳定性,还是里面活跃的物种的多样性,都绝非最佳状态。
这自然是有些历史原因的。当下主管部门对游戏的定位是“文化第一性,商品第二性”,这个标准如今的游戏行业是在努力践行的,但其实九十年代时,《三国》、《赤壁》、《秦殇》、《中关村启示录》这样的作品是完全符合,甚至超越了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较为粗暴的网吧禁令、主机禁令与电击终结了这个时代,并在事实上让出了作品游戏的文化战场。今天一纸《意见》物议如沸,部分来说也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
而我想强调的观点之一,也与这段历史相关。作品游戏战场的丧失,和严厉而一刀切的政策、中小开发者纷纷灰心地退出市场相关,而让出的战场,立即就被海外传入的同类产品挤占了。网游时代进入中国的,都是在文化表达上更有积累、更成熟的外国厂商,而他们的游戏所承载的,是他们认同的价值观。我的博士论文早就指出,我们应当重视游戏,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规模或者就业岗位(虽然这些在提倡数字经济,重视经济稳定性的当下也很重要),而是它培育价值观的能力。
游戏是一种人的本能需求,一种数字时代的基本素养,游戏的冲动与玩游戏的群体都不会消失。我们已经放弃过一次文化阵地,在中国游戏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外国玩家认识有活力的新中国的阵地时,何必自废武功,便宜外人?
已经2023年了,提到游戏的社会责任时,依然在强调防沉迷,是否有点开历史倒车?毕竟哪怕只是我馆,都已经成功孵化、辅助中小学教师使用游戏来完成补充应试教育“育人”责任的美育与德育工作,为什么这种建设性利用不可以成为多方共建的新方向呢?
说到底,游戏产业作为一个一天可以蒸发掉一个京东产值的充满经济活力的产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电影局一样的专业主管部门,而只能通过主管出版的部门来通过版号监管。正是这一现状造成了政策的良好意图与落实动作的变形,带来了产业的恐慌与社会的忧虑。
其实游戏产业在中国存在的这将近三十年间,存在过很多值得一提的智慧的引导与监管政策;针对游戏引发的社会问题,各领域也都积累了值得称道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水库”,这些群体智慧没有转化为行业的历史,也没有能转化为行业的智慧。“游戏局”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希望游戏的专业性得到尊重的学者的妄想,但围绕着游戏及其社会影响,尊重历史,将实践与观点统合到“水库”,是否也是可以逐渐改善事态的一个方向呢?
中国游戏产业如何“而立”?我,一个游戏学者,(自命)产业德鲁伊的理想是,让它成为一个生态学上更自洽的,大中小物种都有,由“智慧的橡树”与“实践的水库”构成的高低错落的森林生境。让它发展、繁荣,顺应自然规律的菩萨心肠,结合钳制不良游戏、不良行动的金刚手段,才能让这片森林能不断向国内外输送优秀的,从中国文化土壤上长出的优秀作品。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因业绩预告披露净利润与实际
因业绩预告披露净利润与实际  第32届中国厨师节在福州举办
第32届中国厨师节在福州举办  生成式AI如何照进新零售?良
生成式AI如何照进新零售?良  水滴保险经纪积极参与“金融
水滴保险经纪积极参与“金融  半导体板块涨3.46% 利扬芯
半导体板块涨3.46% 利扬芯  (乡村行·看振兴)山东特色
(乡村行·看振兴)山东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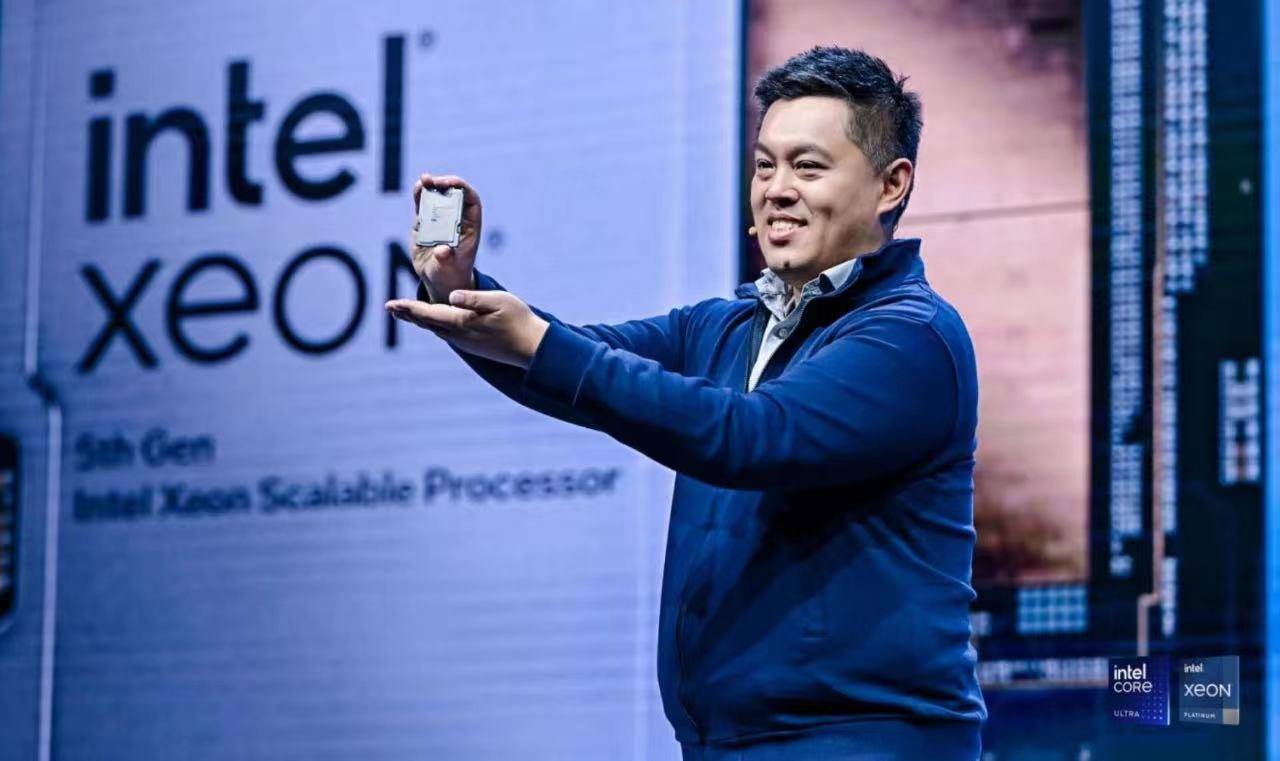 拥抱生成式AI时代 英特尔发
拥抱生成式AI时代 英特尔发  国家开放大学首届新商科创新
国家开放大学首届新商科创新 



